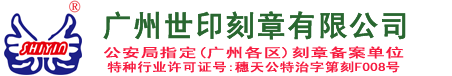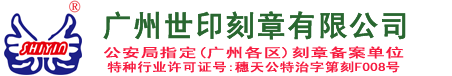示信 ,大概是
印章从古至今最本质的功能和作用。而在先秦,“印”或“章”之字很少用,一般称“玺”。明代徐官在《古今印史》后的《附录诸家之说》录:吾子行曰“三代时无印,《周礼》虽有玺节及职金掌其美恶,揭而玺之之说。注曰:玺,其实手执之印也,正面刻字,如秦氏玺,而不可印,印则字皆反矣。古人以之表信,不问字反,淳朴如此。”刊毅初的“玺”是正面刻字,印出则是反字。但秦汉以来,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,玉玺就成了帝王的专用,“国玺”被视为国家权利的象征。一种尊卑制度也随之而来。何震在《学古续编》十举中举到:“《汉旧仪》:诸侯王,黄金玺,文日:某王之玺;列侯,黄金印,龟钮,文曰:某侯之章;承相、太尉与三公,前、后、左、右将军,黄金印,龟钮,文曰章......’,在这里,印章除了示信功能之外,还被赋予了仪礼文化的内容,而增加了社会等级的制度。特别是在官制系统中,印材的质量,印钮的样式,印文的名称等森然有序。于是,印章开始制度化和规范化。
在示信于他人时,无形中隐藏的是示信人本身,所以,古代
印章中多见示信者官职和个人姓名。有些印章渐渐也用于表征印主人的人格、信念、价值取向、趣味等,于是印章的内容和功能在不断的扩展,出现了“别号印”。别号之兴,肇于唐人,而以之人印的则始于“宋”,何震《续学古编》中二十四举曰:“道号始唐人,以之作印始宋人。”如欧阳修的“六一居士”,苏轼的“东坡居士”等。而这种印章示于他人时,已经明显不同于官印,而更多的是文人的趣味和自我的欣赏。
印章于是也渐渐被用于诗书画的交流中去。潘天寿《潘天寿谈艺录》中指出:“吾国绘画,自北宋以来,题款之风渐起,元明以后尤甚......治印一科,亦随之蓬勃发展。因此印学,亦与诗文、书法密切结合于画面上不可分割矣。”由此可见,宋人始,文人在画面上出现了题款,以诗文补画之未尽之意,印亦如此参与了书画创作,并成为了书画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,很自然地也成了一种艺术。但它被铃用于诗、书、画上,又不同程度地要表示它的示信功能。
诗 、书 、画 、印的结合,也间接地促进了
印章艺术的发展,这也是印章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。印章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印论的发展。集古印谱是文人研究印章的一个标志。除此之外,在印章研究中,文人们也极为重视“古法”和古人的“制度”。随着印章的广泛和自由使用,新的形式也不断出现,文人们除了借研究“古法”,集古印谱来抒发怀古幽情之外,也在提醒着时人一些应该遵循的制度。
本文以用印制度和名号制度为例,既以说明明代文人对
印章的制度的重视,也为当代印学提供古人治印用印规则。 徐官在《 古今印史》中提到:用印制度 :凡卑幼致书于单长,当用名印,平交用字印,草长于卑幼,或用道号可也。反是,则香失之美。凡写诗文,名印当在上,字印当在下,道号又次之。盖先有名而后有字,有号,故也。
由此可见 ,古人用印是极其讲究的,譬如地位低的人致书于地位高的人,或晚辈致书于长辈,应当用名印;地位相当或同辈交流,则可以用字印(名印亦可);而地位高的对于地位低的,或长辈对于晚辈,则可以用道号印(名印、字印亦可)。反过来是违背制度的。那么,在诗文中如用印,名印应当在上,字印、道号依次次之。个中原因是先有名而后有字,有号。
这是有历史依据的,徐官在《古今印史·著述姓名》中记到: 夏、 商尚忠、尚质,称名而已。至周而人文渐开,丈夫之冠也,始加之以字,欲人顾名思义,实有深意寓焉。如孔子名丘,以母祷于尼丘山而生,故字仲尼。伯鱼名鲤,为其生时适有馈孔子鱼者,名与字皆本于此。颜子名回,按古篆“回”字,取义于水,象水屈曲旋转之形,惟渊深则若是,其他则顺流而已,故字之以子渊。曾点字子晰,点字从占、从黑,小暗也;晰字从析、从日,大明也。暗者求于明,扰去尺雾而睹青天也。曾子名参,前倚衡之参,故字子舆。冉伯牛、司马牛,皆名耕,盖牛之为用专在于拼,是之取尔。端木踢,字子贡;韩愈,字退之。一则取上予下献,君臣相交之义;一则取卑以自牧,不敢先人之意。温公,字君实;文公,字元晦。非数华就实之谓乎?司马相如,字长卿,长字当读如长上之长,以蔺相如为赵之上卿,故云长耳。蔺乃贤者,既同其名,复效其职也。牛僧孺,字思黯,以汲黯,字长孺,黯称忠直,故名取其字,字取其名也。范文正,名仲淹,字希文,以王通,字仲淹,似谧文中子,为一代之儒,故名亦取其字,字则希其谧耳。乃若苏氏二子,字说皆可取法者也。玩古人命字虽不同,而其取义各有彼当,官特举其有关于大义者,表而出之。
纵观以上内容可知,古人原先只称名,人文渐开之后才有了字,而字多顾名思义,深寓名之意,多用于表德。是有了名之后才生意。道号亦是如此,道号也是用于取义。徐官又记到:或因性急 ,而以“韦”自勉,或因性缓,而以“弦”自砺,有思亲而号“望云”,有隐江湖而号“散人”,纷然不同,然皆士流则有之。今也不然,而香吏之徒,往往而有以号者众也。恒虑其相同,崇尚新奇,有名“木”者,号曰“半林”,有性“管”名“萧”者,号曰“四竹”。
可见 ,道号也是用于表意的,而更多的用于表一种意趣或信念,相当于字来说,可以次于字。那么,在铃印的顺序上就应该有所区别,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在宋、元诸儒真迹中用印,大多是这样。可是在明代以前并非如此,徐官认为是今人不太规范的作法:试看宋 、元诸儒真迹中用印皆然,今人多不讲此。或曰:印有大小,小印用于上,大者用于下,庶几相称,此世俗之见也。只论道理当何如,印之大小何足云?
徐官所谓的今人,当然相对于宋、元而指的明代人。其实,由印的大小顺序铃印,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因为到了明代,印章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有机地参与人书画艺术中去,考虑到画面的整体性,印章这样使用是可以理解的,虽然有失“古法”。